區選制度源頭 洋學者夫婦揭荃灣50載變遷(多圖)
發布時間: 2019/11/18 22:41
最後更新: 2019/11/24 15:57

▲ 1960年代末的荃灣街市街、眾安街一帶有攤檔、酒家、商會、工會、體育會、中醫館,熱鬧而紛雜。(受訪者提供)
區議會選舉周日能否如期上演仍未可知,追源溯始,整個制度原來源自1970年代的荃灣,官方冀能聆聽、疏導日益複雜的民情,乃成功的政治實驗。
「荃灣為香港的管治充當了先鋒。」1968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生詹森(Graham Johnson)跟太太兼同學羅碧詩(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結伴來港,雙雙選以位處城鄉邊界、新舊居民混雜的荃灣為論文,兩人退休後耗5年把近半世紀的研究合撰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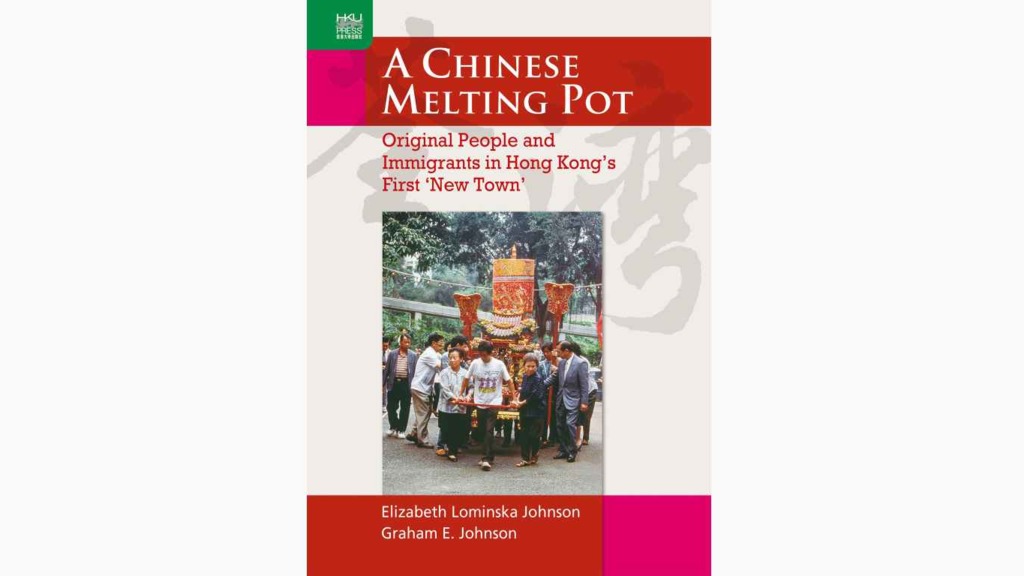
據兩人近月由港大出版的《A Chinese Melting Pot》所指,無論管治到看法,英國對1898年租借的新界素跟港九迥異。
然而,二戰後20年間,荃灣的工業極速發展,人口暴增了40倍。71年荃灣(包括今天葵青區)已是香港最大工業區,佔總工業產值兩成,涵蓋油庫、造船、紡織、石灰、燒磚、搪瓷、醬油、樟腦片等,也有家庭手作如蛋卷、家具、掃帚等。


單靠看重村民利益、鮮涉足工廠的鄉事委員會任中介,漸漸捉襟見肘,
原居民領袖不甚了解新移民的問題和困難,不少層面也不及移民領袖見多識博。
二戰後20年間 人口暴增40倍
當時,移民人口社團多元、鬆散,有權勢的上海南來大廠家卻不怎理會,故沒門路直達區域官員,如大窩口徙置區的街坊福利會便難知應以理民府還是徙置事務處為先。本已極擁擠的唐樓、寮屋,加上葵涌道、青衣橋帶來的新建公營房屋居民,全令荃灣成為麥理浩港督任內最棘手的新界區域。
終於,荃灣理民官許舒(James Hayes)1976年創先河兼任「市鎮專員」,打破官僚制度樊籬,獲派更多人手整合處理市務。同年,麥理浩拍板成立「荃灣康樂市容諮詢委員會」,冀發動民眾參與規劃和服務,找來區內活躍領袖主責,成果有藉公開比賽選出、沿用至今的區徽,相類諮詢制度翌年擴至全新界,為後續機構區議會1982年先後於新界及港九首辦普選奠基。
香港的所謂『第二梯隊』管治可是76、77年首先在荃灣創立和實驗。
2007年自加拿大卑詩大學社會學系退休的詹森越洋受訪道。現居溫哥華近一小時機程外小鎮,夫婦坦言廣東話已生疏,惟羅碧詩仍幾乎每天跟荃灣關門口村契女一家等老朋友短訊、通電。比起當初在港要寄信聯絡家人和論文導師,天壤雲泥。
「太沒規劃滿是寮屋 一塌糊塗」
港府正檢討應否續製的《香港年報》,來自英國的詹森憶述,研究荃灣的伊始正是堪稱當年唯一資訊來源的年報,他很想知大嶼山石壁水塘和青山大欖涌水塘工程逼遷的村民怎融入荃灣新生活。詹森的博士論文最後聚焦荃灣移民人口如何應對經濟、社會急速變更,羅碧詩則探究多姓原居民村不同譜系和家庭的變化。
「荃灣是新界一部分,卻與別不同。」迄今難忘元朗絲苗米之味的詹森謂,六七暴動後幾為僅4個月大兒子的安全放棄來港,最後一家如願踏足正高速工業化的荃灣,始終不禁訝異於眼前境況。原籍美國的羅碧詩續道:
它太沒規劃,房屋混亂不堪,滿是寮屋,真是一塌糊塗。

1958年,港英着手研究發展荃灣成「衞星城市」,首度正式嘗試規劃,但面對陳廷驊、查濟民、曹光彪等江浙廠家促成的人口、經濟發展已有心無力,如多條原居民村包括舊關門口村(現熊貓酒店一帶)變成位處青山公路之下,水浸頻仍,官村只好談判搬遷。兩人指,70年代發展的新市鎮如大埔、元朗皆引荃灣早年缺失為鑑,包括特設工業邨。



詹森坦承,英籍當年確帶來方便,如可免簽證來港,大概也為查看官方紀錄打開方便之門。「有人會覺得我們是政府間諜。」羅碧詩不禁失笑,她們應是荃灣僅有的洋人居民,更靠時任理民官班禮士(Graham Barnes)先後住進區內唯一現代中產住宅華都戲院大廈(祖籍上海的邱德根所建)及新關門口村(現大窩口港鐵站上方),
我們解釋有政府、大學資助支持生計時,他們大概不怎能理解吧!
兒子打破隔閡 令全家更人味
夫婦盡量講中文,羅碧詩打扮得像關門口婦女,詹森深信兒子詹德力對打破隔閡、融入社區居功之偉,令全家更有人味。這個大家暱稱「巨仔」的小孩在孭帶上高呼叉燒、蕎頭時,商販總有求必應,
他那時很趣致,可受歡迎了!是個金髮藍眼的華人男孩!
詹森一家常接觸原居民,
當我兒子遇上老人、老婦,總自動由廣東話轉成客家話。
潮州人多賣熟食 客家人賣菜
縱然大致相處融洽,始終人以群分。專研荃灣組織、領袖的詹森發現,小販之中,潮州人多賣熟食,客家人賣菜,操粵語的東莞人則主攻水果,「山上寮屋區以潮州話主導,市中心會聽到四邑話,紡織廠工頭則講上海話。我所認識的荃灣上海人中,能講廣東話的只有必須操雙語的教師。」


荃灣曾見證國共兩黨明爭暗鬥,56年的雙十暴動死了8人、損失25萬元,詹森指及至60年代末,關門口仍有平素極友善的左派領袖,純粹出於政治連繫拒絕受訪。他相信,70年代,麥理浩時代引入9年免費教育,以及廣東歌的冒起,是港人身份漸漸成形的要因。再者,內地10年文革動盪,也促成額外的政治、文化鴻溝,「跟香港的流行文化大相逕庭。」
中國改革開放後,詹森指不少人類學家可直接前赴四川、福建等地,香港的研究地位有所下降;然而社會學者近年從佔領中環起,對港人和社運的關係有新興趣,「惟盡管荃灣對香港舉足輕重,(學界)普遍仍視若無睹。」
兩人學成入職卑詩大學後,仍不時回港研究和探望友人,前後在關門口住約7年和5年,關門口搬村50年、九七年回歸等大日子俱在場,羅碧詩對主權更替前夕記憶猶新:
村長老齊集土地公、伯公,稟報政府行將改變,祈求繼續受保佑。



雖然好友許舒上世紀90年代所寫的《滄海桑田話荃灣》儼然已成各方權威參考,羅碧詩指此類繙譯極艱巨,新作暫未有計劃出中文版,「但我們樂見不諳英文的荃灣朋友都能讀到。也感激港大出版社能包括中文字(註釋)。」

全文刊於《經濟日報》(付費閱讀),標題及內文經編輯修改。
撰文 : 經濟日報記者 姚沛鏞







